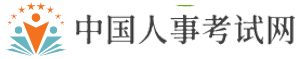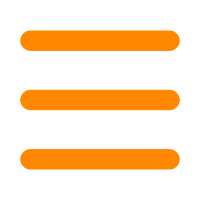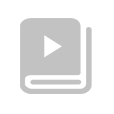《庄子.天道篇》中有一个桓公与轮扁的故事。故事说,有一天桓公在堂上念书,工匠轮扁在堂下斫车轮。轮扁看见桓公读得津津有味,十分投入,就放手锥凿走上前来,问桓公读得是什么书,为什么这样入迷?桓公答曰,读的是圣人之言。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桓公回答,圣人已死。听到这话,轮扁就说,主公,非也,你读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桓公听罢大怒,定要轮扁给一说法。于是,庄子就借轮扁之口,说出了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印于心,口不可以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可以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可以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子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1]
庄子的这一故事涉及到现代哲学讲解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关于大家所要理解和讲解的文本的书写,言说到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桓公看来,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伴随圣人的死亡而消失。它通过圣人的言谈、书写保存下来,流传开去。今天大家理解圣人典籍的本义,就是要通过聆听圣人之言,阅读圣人之书来达到。换句话说,流传到今天的圣人之言,圣人之书与作品本义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这类圣人之言和圣人之书乃是大家今天通向作品本义的唯一靠谱桥梁。与桓公的这一立场相左,轮扁用他几十年斫车轮的经验说明,一个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可以毫无妨碍地通过作者的言谈和书写保存下来,流传开去。作者之言、作者之书非但不可以成为判断作品原义的最后依据,相反,它们总是成为妨碍大家达到文本的真实意义的屏障。
应当指出,尽管桓公与轮扁在关于语言在理解过程中有哪些用途,在关于文本的书写、言说到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答案完全不同,他们所持的根本哲学立场可能却相差不远。比如,桓公好像也认定每一文本都有一真实固定的意义,可能甚至并不反对轮扁关于这一意义可通过作者的“得之于手而印于心”的渠道去达到的说法。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与争论仅仅在于觉得这一意义是不是与怎么样“能言”,或者说,只在于觉得这一意义能否与怎么样通过语言被别人理解和传达。所以,从现代讲解学的看法来看,庄子及其后学在这里尽管涉及到知道释学的根本问题,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则好像太过于简单和偏颇。
那末,真的存在着独立、客观的文本意义吗?在现代讲解学哲学家的眼里,一个作品(文本)的“客观”意义与读者的“主观”理解和讲解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作者、作品(文本)、读者间因为语言(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历史、文化、地域而产生的间距到底是理解和讲解的障碍还是理解和讲解得以可能的条件?文本讲解能达到“真理”吗?假如能,那样这种“真理”在什么意义上为“真”?本文以下将重点通过讨论法国现代讲解学哲学家利科关于文本与讲解的思想,以期能对上述诸问题的回答找到某些启示和线索。
2、文本、言谈和书写
在“讲解学的任务”一文中,利科将讲解学初步概念为“关于与‘文本’的讲解有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作为当代讲解学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也说讲解学是从“对文本的理解艺术”开端。[2]这样来看,讲解学的任务就是对文本的理解和讲解。
那样,什么是讲解学意义上的“文本”呢?利科第一说:“文本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言谈”。[3]关于对这一说法的传统讲解,利科的讨论依据的是十九世纪瑞士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结构主义哲学的先驱索绪尔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的区别。在索绪尔看来,所有些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的结构部分,它是常见的、社会的、共时性的和不依靠于具体个人的,其次是言语的行为部分,它是具体的、各别的、历时性的和异质性的。在大家的语言生成和进步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而且互为首要条件的:要言语行为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所有成效,需要有语言结构;但要使语言结构可以成立,也需要有言语行为。”[4]在语言结构与言语行为区别的基础上,索绪尔定位书写文字的地位。索绪尔说:
语言与文字是两种不一样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块,结果纂夺了主要有哪些用途;大家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的和这符号本身一样要紧或比它愈加要紧。这好象大家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5]
如此,大家从索绪尔那里得到了一幅由语言结构到口语言谈再到书写文本的逐步以降的图画。由于书写的文字只不过言说的语词的表现,并无加入任何新的成分,所以书写的文本低于口语言说。
利科对索绪尔的这一语言、言语和文本关系的传统讲解不以为然。利科指出,从讲解的角度来看,在传统的关于语言的学说中,不加思索地给予语音以优先地位是大有问题的。一般讲来,虽然所有能写出的就一定能被说出,但书写肯定还可以表明一些“超出”言说的东西,不然的话就没书写的必要。也恰恰是书写的存在才更多地引出和说明讲解的重要程度与必要性。在利科看来,文本所赖以打造自己的书写阅读关系与言说所赖以打造自己的对话问答关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对话乃对话者之间通过言说、问答的直接交流。与对话相比较,文本的书写与阅读则缺少这一层直接的交流关系。这也就是说,在书写和阅读、作者与读者之间,有一时空的间距。因为这一间距,读者在作者写作时,作者在读者阅读时缺席。利科将这一现象称为文本主体的当下“双重消陨”。也正是因为这一消陨而产生的间距使得“书写的文本”具备“建设性”。这一间距也大家意识到,应当是文本而非作者或读者占据着理解和讲解的中心。用利科我们的话来讲就是,
书写使本文相应于作者意图的自主性成为可能[6]。
如此说来,文字书写,也只有当它逃脱言说的禁锢,不再被视为后者的誊本或赝本,才真的意味着其作为文本的诞生。也就是说,作者的“死亡”同文本的“诞生”是同时的。
有时我想说,阅读一本书就是要将它作者视为已经死去了,将此书视为作者的遗著。由于只有当作者已经亡故,此书的意境关联才会如其本然所是的那样完整无缺。作者不再可以响应,所剩下的就只有阅读他的作品。[7]
一旦文本取代了言谈,就不再有说话者。[8]
第二,将文字书写从对话言说的阴影里解放出来不只标志着文本主体的“死亡”,而且同时也意味着文本语言与它所意指的世界的关系的重新理解。大家了解,语言,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是通过符号、语句的形式述说关于世界中的某个事物、事件或某种局势。利科指出,语言的这一“关于什么什么的述说”的结构一方面表明语言与它所述说的或者所指向的“世界”之间总有一个间隔、一段距离;其次它也表明述说行为本身就是要在这之间消除间距,架起桥梁,从而使“世界”展示出来。但,利科又指出,在口头对话与文字阅读的状况下,语言所指的“世界”的展示情形是各各不一样的。在口头对话中,世界“表现”出来,而在书面阅读中,世界则是“再现”开来。
大家或许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讲明利科的这一看法。假设有一对夫妇,大李与小梅。大李下班回家,小梅告诉大李:
(1)“宠物猫吃掉了蛋糕。”
大李一下子就了解了小梅的意思,原来今天是大李的过生日,小梅在沮丧地抱歉她的宠儿宠物猫吃掉了她为大李筹备的过生日蛋糕。因此,小梅说的是
(1a)宠物猫吃掉了蛋糕。
大家了解,在这一口头对话的情境中,“宠物猫吃掉了蛋糕”这一语句的意义舆其所指称的世界‘宠物猫吃掉了蛋糕’之间的连接因为说话者大李与小梅与围绕他们的周遭环境的“在场”就一下子变得一清二楚。所以,利科说道,
在言说中,说话者不只相互之间在场,而且,言谈时的处境,周围的环境也一道在场。正是在对这一周遭环境的意境关联中谈话获得了其全部的意义,...因此,在活泼泼的谈话中,所说出的话语的理想意义指向那实质的所指,即指向大家所说的东西。...意义蔽入所指,而所指则蔽入当下显现之中。[9]
但,在文字阅读中,情形则大不相同。不只说话者不在场,言谈时的处境与周遭环境也都隐而不现。文本的所指不再当即显现。这一文本与文本的所指之间的延搁或悬搁现象并不意味着在文本阅读中,不再有文本的所指,而是说文本目前不再直接指向显现的世界。它从当下世界的显现中“自由”出来,指向其它的文本。根据利科的说法,与阅读文本有关的其它文本有哪些用途在阅读中就等于说话者的处境与周遭环境在言谈对话中有哪些用途。比如,在大家上面给出的例子里,当我不是作为对话者听到而是作为读者读到(1)“宠物猫吃掉了蛋糕”时,展示在我面前的并不势必就是(1a)的世界,即‘宠物猫吃掉了蛋糕’,由于谈话者大李和
小梅与随着他们的实质周遭环境全都退隐不现,或者说作为读者的我面临的文本所指向的是种种的可能世界而非某个现实存在的世界。如此的话,除去第一种状况,即1(a),我还可能遇见如下的种种状况:
状况2:可能早晨上班前大李与小梅打赌,说宠物猫不会吃蛋糕,由于他只见过它吃鱼或者买来的猫食。大李走后,小梅拿出一块蛋糕喂宠物猫。宠物猫吃了蛋糕。
假如上述可能世界为真,那样,当我读到(1)“宠物猫吃掉了蛋糕”时,我应当将之讲解为
(1b)宠物猫吃掉了蛋糕。
也就是说,小梅说这话的意思是告诉大李他输了,宠物猫不是不吃蛋糕。
状况3:可能这两天宠物猫生病了,厌食不吃东西。早晨大李与小梅还为之耽心。所以,当大李晚上回来,小梅便忙不及地告诉大李
(1c)宠物猫吃掉了蛋糕。
这里,小梅想说的是,宠物猫今天吃掉了蛋糕,说明它的病有所好转。大李不必再为宠物猫耽心了。当然,大家还可以设想各种各样的其它可能情形。在这种种不同文本的意境关联下,语句“宠物猫吃掉了蛋糕”作为文本(1)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意义,比如(1a)、(1b)、(1c)、等等。由此,利科得出结论,
任何的文本,伴随它与其世界的关系的消隐,就获得了自由,并将自己投入到与其它文本的关联中去。这种与其它文本之间的关联取代了在活泼泼的言谈中被指称着的周遭现实的地方。这种文本与文本间的相互关联,就在作为大家言谈所及的世界的消隐中,促生了文本或者文学的“准世界”。[10]
所以,对于阅读活动而言,大家作为读者,面对的就是如此的一个好像“既无作者,又无世界”,自主独行却又相互关联的文本世界。利科将这种文本的自主性又讲解为“文本相应于作者意图,作品情境与原初读者的独立性"[11],而正是因为这种独立性或自主性,文本的讲解才成为可能。于是乎,内在于文本的本质中的文本与原作者与与文本所指的当下世界之间的时空间距非但不成为妨碍理解与讲解的屏障,相反,它应当是真的的理解与讲解成为可能的源泉和必要首要条件。
3、狄尔泰的主体讲解与结构主义的文本说明
就其本质而言,阅读是一种理解与讲解行为,因此,它涉及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在大部分讲解学哲学家看来,重点的问题并不在于询问阅读作为理解与讲解是不是可能,而在于描述这种理解与讲解是怎么样在事实上发生的。为了可以真确地描述理解与讲解的发生过程,利科第一批判性地考察了现在有影响力的两种讲解理论并将之作为我们的思想资源。
利科第一考察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主观讲解理论。大家了解,狄尔泰常识学说的基础在于分析与理解的区别。在狄尔泰看来,所有科学常识的对象范围无非有两个,一个是外面自然,一个是精神心灵。自然科学立足对于客观世界对象的察看和说明,并且这种察看与说明遵循着数学演绎与总结逻辑的路径。与之相应,历史精神科学乃是关于心理主体、生活和精神的科学,它探究人的精神、心灵与其表达的历史与生活。前者致使科学分析,后者则引向心灵理解。这也就是狄尔泰的名言“大家分析外面自然,但大家理解心灵生活”[12]的意义所在。
既然理解是一种心灵间的交流过程,那样就其本质而言它就是“主体间”的。用狄尔泰的话来讲就是,理解乃是“对别人与其生命/生活表达的理解”。而讲解则体现为理解主体生命/生活的渠道或办法。狄尔泰将人的生命、生活的表达分别分为常识、行动、精神的体验表达如此几个种类并指出每一种表达种类都有其简单与复杂的形式。这种讲解和理解既是心理的,主观的,又是逻辑的,客观的。当这里说讲解与理解是心理的、主观的,狄尔泰指的是每一种讲解作为理解的过程都是作为读者的主体,在日常,在历史中,经由移情想象把自己置入别人的境况而与作为作者主体的别人之间的心灵精神交流。当说到讲解和理解又是逻辑的、客观的,狄尔泰是说这种移情想象与主体间的心灵交流在历史、精神科学中需要通过对符号、文本,特别是对艺术作品与历史经典的阅读和解析来达成。而这类符号、文本、艺术品、历史经典作为内在生活的外在表达与历史生活的如今表达乃是作为读者的我和你与作为作者的他或者她之间共有些。因此,符号、文本的存在与它们在大家阅读过程中的角色与用途就使得大家从理解的个别性、主观性中脱离出来和升华起来,从而达到历史精神科学中讲解和理解的客观性与常见性。
但,问题在于,符号、文本、艺术品和历史经典作为作者主体的内在生命与生活的外在表达是在什么意义上,又是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一种科学的与逻辑的常见性与客观性呢?假若理解需要从主体的内在生命与生活的体验出发,讲解到底能否达到常见性与客观性的目的呢?应当说狄尔泰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尽管一定,但无疑也是不那样让人信服。狄尔泰曾以他一个人阅读路德的经验为例说道,
当我浏览路德的信件和著作、他同年代人的评论建议、宗教大会及议事会的公函律令与他本人的正式文件时,我就历程和体验到了一个这样具备震惊力的,在严格的意义上生死攸关的宗教性过程,而这一历程和体验完全超出了其他人今天的经验以外。……大家依据下述关系就能体验到路德的思想进步:这种关系从全人类的共性浸透到宗教范围,并通过其历史规定,又从宗教范围浸入他的个性。如此,这一过程就为大家打开了一个他与他早年宗教改革年代的同仁们的宗教世界。[13]
狄尔泰在这里谈论自己阅读路德的特别体验当然无可厚非,但他进一步宣称这一体验触及到了“全人类的共性”和常见性的“年代精神”就看上去是一依据不足的“逾越”了。大家甚至可以说在这里看见了黑格尔绝对主体性的影子。正由于这样,利科不认可狄尔泰这一经由主观讲解达到客观理解的立场。利科对狄尔泰的主观立场曾有一很精辟的概括,他说,
理解寻求一种与作者的内在生命/生活的相契和相同。它试图再造那使作品得以产生的创造性过程。……虽然生活的外在化是更多意味着对自我与别人讲解的某种间接和媒介性质,但正是在心理学意义上的这一个与那一个自我才构成讲解诉求的对象;讲解一直以生活经验的再生、再建为目的的讲解。[14]
在利科看来,狄尔泰的这种将理解概念为主体间的心灵交流并将讲解视为经由阅读符号、文本为达到理解的一种客观化的渠道的说法反映出狄尔泰的讲解定义中的心理学主观基础与逻辑学客观目的之间的不谐和冲突。尽管狄尔泰自己在其思想的后期阶段,也不断地尝试摆脱这一不谐,但他一直未能超出浪漫主义讲解学主体讲解的阴影。关于这一点,加达默尔也过去有过一针见血的批评。在加达默尔看来,对于狄尔泰和其它浪漫主义讲解学哲学家们来讲,
每一次与文本的接触都是精神的一种自己与我们的接触。每个文本既是陌生的,由于它展示为一个问题,又是熟知的,由于该文本在根本上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大家可能对于该文本所知甚少,但只须了解它是文本、著作、是精神的某种表达就足够了。……历史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可理解的,由于所有都是文本。[15]
假如说对狄尔泰的理解讲解理论的批评考虑构成了利科文本、讲解理论的要紧背景来源之一的话,他对当代结构主义的有关文本结构的解释说明理论的批判性的剖析就应当被视为另一要紧背景来源。与狄尔泰强调讲解的主观方面,强调作者与讲解者的心灵交流不同,当代结构主义的作家们则强调讲解的客观方面,即文本本身的结构在理解讲解中有哪些用途。文本,就其本身而言,并非如狄尔泰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作者生命、生活体验的外在表达方法。文本一旦被创作出来,就与作者“绝缘”,也不完全受它所意指的世界对象的束缚。作为语言现象,它既不被哪个说,也不跟哪个说,也不针对什么说。它只不过自说自话,展开我们的结构,达成自己的功能。正如利科所说,
文本不像言谈那样要对哪个说,就什么而说。它无超越的目的,只向内,不向外。[16]
就办法论的层面而言,结构主义的讲解理论不像狄尔泰的讲解理论那样依靠于以主体交谈为中心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它更多的是从与文本阅读有关的语言学吸取养料。所以,语言的话语结构剖析就成为结构主义文本讲解的向导。
利科举出俄罗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弗‧普罗普关于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结构剖析与法国文化人类学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原始神话的结构剖析作为例证。在普罗普上世纪二十年代写成的《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一书中,他剖析了一百个俄罗斯传统的民间故事。他发现,这类民间故事一方面不乏丰富多彩的情节内容,但同时又具备好像如出一辙的叙事结构的诸功能。普罗普觉得,所有些这类俄罗斯民间故事不出三十一个叙事功能和七个行动范围以外,它们具备相同的结构种类。但,故事的功能与范围具体由哪个达成,怎么样达成则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它们就构成故事的可变因子。尽管因为这类可变因子的原故,每一个故事的情节各各不同,但由于它们的叙事功能却是恒定的,所以从整体上看,所有故事的叙事结构是不变的。斯特劳斯关于原始神话的结构剖析也是一样,但他更多的关注叙事的关系结构,而非功能结构。在斯特劳斯看来,组成神话的诸单元,或者“神话素”之间并不是无逻辑和无连贯性的。一个神话的意义应当从神话素结合的方法中去探寻。比如对著名的俄狄浦斯神话,斯特劳斯列出四个竖栏ABCD,每一竖栏包括有不一样的“神话素。”当大家阅读这个故事时,大家沿循故事的自然关系,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横着读。但当大家要理解这个故事时,大家则应当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一竖栏,一竖栏地读解。在斯特劳斯看来,A栏和B栏,C栏和D栏在俄狄浦斯神话中,构成两两对立的结构态势,而对这一结构态势的体认,就使大家理解到俄狄浦斯神话的意义在于揭示自然与文化的紧张与对立。
在利科看来,尽管结构主义哲学家们从二十世纪语言学与符号学的最新进步出发,从文本自己的语言结构剖析入手,在文化人类学、民俗研究、神话研究与文学批评等范围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种结构剖析至多仅构成了一种关于神话和传闻的科学“说明”,而还没达到哲学讲解的高度。这也就是说,结构主义夸大了在讲解过程中文本对于讲解主体的读者、作者与其创作、解析情境世界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们不是把后者看作被暂时地“悬搁”,而是永久的离别。如此,他们事实上剥夺了自己在文本意义讲解方面的发言权。其次,结构主义所持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独断论”立场。它好像预设文本只能有一个内在客观结构。这一预设假如仅仅局限在语言学或者语文学的研究上,好像还有几分道理。但,一旦将之延展到所有人文、历史学科并将之视为其办法论基础,就立刻大有疑问了。比如,即使对于俄狄浦斯神话的讲解,除去斯特劳斯的语言剖析结构外,还有著名的弗洛依德的心理剖析的结构。假如两种都是科学说明的话,哪一种说明更为真实呢?或许,本来关于“说明”与“讲解”之间的绝对界限就是没有的,所谓科学的“说明”只是一种讲解主体表面上被隐藏起来,但暗地里仍起著用途的“讲解”罢了。
[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