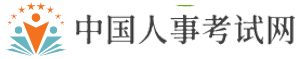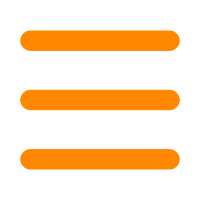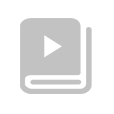[摘 要]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非常重要的经典。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既需要对这本著作有一种整体的见地,也需要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渊源加以考察。从海德格尔的思想渊源来看,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办法是源于胡塞尔和狄尔泰的“讲解学的现象学”,而《存在与时间》的实质内容就是源于克尔凯郭尔的“存活主义”。从《存在与时间》整体的叙事结构来看,整个著作分为层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从平时生活的讲解学,到清醒的畏的意志论及其对平时状况的否定,最后到本真的存活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及其对前两个部分的重新讲解。
normal align=center>
海德格尔的哲学的根基在于现象学,这毫无疑问。没胡塞尔的现象学所开辟的道路,就绝对不会有海德格尔的哲学。胡塞尔常对海德格尔青梅煮酒论英雄说,“现象学,你我而已”。在胡塞尔的指导下,海德格尔从事“宗教生活现象学”的研究。1928年,他作为继承人接替了胡塞尔在弗赖堡大学的教席。到了1930年,胡塞尔已经十分确定地觉得海德格尔背离了现象学精神,倒向了象舍勒那种哲学人类学和历史相对主义的东西了。胡塞尔在一本《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苦涩地写道:“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amicus plato, magis amica veritas)。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的贡献在于《存在与时间》中的“讲解学的现象学”。即便在他不再用讲解学,或者说他不再运用讲解学的现象学的办法时候,海德格尔仍然是一个现象学家,尽管对此施皮格伯格有所保留。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讲解学的现象学显然除去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源头以外,还有狄尔泰的讲解学源头。海德格尔自己说过,他逐字逐句地阅读过狄尔泰的要紧著作。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讲解学和历史主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狄尔泰对存活和思想的历史性的洞见使得海德格尔可以突破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范畴直观和意向性、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的常见有效性与拉斯克的生活深思性范畴。于是大家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吸收并超越了主宰当时德国思想界的三大哲学流派:德国东南马堡新康德主义学派、胡塞尔的现象学派与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学派。
假如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办法是讲解学的现象学的话,那样《存在与时间》的实质内容就是“存活主义”。尽管海德格尔在其晚年一再声称这部没有完成的著作只不过从此在的方面探讨了存在的意义,而没从存在本身去考虑存在的真理和历史,因此是片面的,但,这部没有完成的著作仍然产生了爆炸性的成效,并引发了德国与法国的“存活主义”的哲学和文学运动。海德格尔在1945年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批判只能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但并不可以不承认《存在与时间》与克尔凯郭尔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与它对《存在与虚无》的决定性影响。在《存在与时间》之中,大家会更多地谈论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显然,海德格尔的克尔凯郭尔不再是基督教作家的克尔凯郭尔,而是一个被尼采的历史主义的无神论洗礼了的克尔凯郭尔,因此大家可以说,海德格尔是在克尔凯郭尔与尼采之间进行考虑的。
在二十世纪初期,死时年仅42岁的丹麦人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成为席卷德国的思想家,由巴特、戈加滕和布尔特曼掀起的二十世纪第一场神学革命即辩证神学所推崇的先驱就是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在《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中使克尔凯郭尔成为一个存活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只不过从克尔凯郭尔那里学到了存活的“极限情境”的定义。只有通过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才被转化成哲学的定义进入哲学范围。有不少人都看出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哲学术语是来自基督教的,但事实上是来自基督教作家克尔凯郭尔的。坐落于海德格尔思想核心的“常人”、“畏”、“死”、“罪”、“良心”、“决断”、“重复”等定义无疑是来自克尔凯郭尔的。只是,在海德格尔这里,人的存活不再是在与上帝的无限的距离的信仰的存活,而是尼采式的存活“在世界之中”。
看着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1843)中需要在审美的生活和伦理的生活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决断,但他一个人却选择了非此非彼的宗教生活。这三种不一样的存活道路作为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主题第三出目前《生活道路的诸阶段》(1845)中,这本书更多地沉思了信仰的宗教生活。在此后的著作中,克尔凯郭尔完全致力于沉思信仰的存活方法。对人的信仰的存活的辩护使克尔凯郭尔在《<哲学片段>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中淋漓尽致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讲解了被后人视为存活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即主体性”的思想。海德格尔正是从克尔凯郭尔这里去理解“存活”和“此在”的定义的。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它所完成的部分的核心部分乃是“此在与时间性”,整部书的导言和对此在的预备性的剖析这两部分相对地居于次要的地位。因此,大家好像可以说《存在与时间》根据所完成的部分毋宁叫做《此在与时间性》。虽然海德格尔多次指出要从存在来规定此在这种存在者,但此时他只不过从此在与存在之间的这种讲解学循环,这就意味着他是从此在的讲解学去理解“存在的意义”,而不是从存在本身的现象学去理解“存在的真”。与此相应,海德格尔也没直接论述时间的存在方法是什么样的,而是从此在的时间性出发去讲解时间本身。在《存在与时间》的结尾,海德格尔念念不忘地说,此在与时间性只不过一条通往理解存在与时间本身的道路。海德格尔的确在他晚期的哲学中达成了这一转折。但,在《存在与时间》中,大家还是沿着海德格尔本人所谋划的很精致的叙述结构去理解他的“存在主义”吧。
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的办法在描述此在的存活的时候,第一确立了原原本当地接近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的方法。这就是从人的平时生活出发。海德格尔将人的平时的平均的存活状况视为理解此在的存活的起点和基础。看着,海德格尔对人的平时生活这一基本的原初的事实性的关注具备明显的反学院、深思辨的倾向。但大家不要忘了这只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出发点而已。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分的平时生活的讲解学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基于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现象学的讲解。在这一部分中,展示了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精神重新解析古典哲学的技艺,这一技艺对于二十世纪哲学具备重大的意义,从他那里大家看到了一种阅读的技艺,这一技艺致力于恢复伟大的哲学家的文本中那种彻底的源初的考虑。在和韦伯、耶格尔、卡西尔、哈特曼这类当时的权威学者对比之后,当时不少青年都感觉到了海德格尔思想远为强大的力量。海德格尔在马堡的五年(1923-1928)执教期间,既是他思想迸发、最有收成的时期,也是他与阿伦特相爱的甜蜜时期,也是他吸引整个德国的年轻人才俊追随他学习哲学的时期。当时除去马堡三杰洛维特、伽达默尔、克吕格以外,阿伦特、马尔库塞、约纳斯、安德斯等人都在海德格尔的课堂上。施特劳斯、沃格林和库恩等人也都遭到过海德格尔非常大的影响。到了《存在与时间》出版后的三十年代,海德格尔的课堂已经培育了一代阵容庞大的德国哲学家。这是二十世纪最为壮阔的学院之内的哲学教育运动。
人的平时生活向大家展示了存活现象的丰富性。海德格尔将人的平时存活状况规定为“在世界之中”。这个在世界之中的存活,根据现象学的见地来看,并非一种呆板枯燥、千篇一律的东西。相反,它以一种新鲜的见地看到了“在世界之中”意味着存活与其周围世界的丰富的关联性。“在世界之中”并非象石头放在口袋里一样,而是活生生存活的人居住在他所熟知的周围世界。因此,“在世界之中”意味着人只栖居在此世之中。这是一个尼采式的断言。“在世界之中”是此在通过用上手的用具而拥有些一个相互牵连的有意义的整体的世界。传统上所谓的客观世界或者实体化的客体从这种此在的现象学的见地来看,只不过一种对象化的认识立场,并非此在所存活的周围世界原原本本呈现出来的实情。不只这样,海德格尔在此还很小心地留下了一笔,他说真的的自然和世界仍然是隐藏的,真的的世界不是用具的世界,物性也不可能被用具的规定所穷尽。这就是他晚年所思的事情。
人的平时生活状况并不止是一个用具的整体所牵连出来的周围世界,而且人还和其他的人一同“在世界之中”。正是通过“共在”,这个世界才形成一个一同拥有些世界。此在就在这个一同拥有些熟知的平时的平时生活的世界中。但,一般与别人一同生活与在世界之中的平时状况的此在并非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常人”,一个匿名的人群。这种“常人”状况一般说来一直第一成为此在的存活方法。这种在每一个此在身上的常人并非一个具体的人,更不是所有人,甚至在无人的时候常人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就象是穆齐尔在《没个性的人》和黑塞、本恩等人在诗歌里所写到的,与大家在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中所看到的。然而,海德格尔看着并非一味地批判“大家的独裁”,而是声称常人的在世界之中对于领悟人的存活都具备肯定的积极意义。这个积极的方面何在呢?或许就是海德格尔要堵住大家向此世以外祈求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安慰的道路吧。
假如大家可以用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五卷中的一个比喻的话,那样大家可以说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叙事结构也有“三波浪头”。这里对平时生活的讲解学地展示只不过这部书的“第一波”。看着它好像象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对传统的认识论和理论的批判,也非常象那些不满于学院哲学的人对传统形而上学(也包含当时时尚的新康德主义)发出的一种反叛的和回归的冲动,有些地方象是打造某种平时生活或生活世界的哲学,或者是一种常人剖析的办法论……这部书如果仅仅到此为止的话,这类假设都大概。但假如大家还是从克尔凯郭尔对人的存活的沉思来看的话,大家可以说,这只是“生活道路每个阶段”中的第一种道路或第一段道路。
在“第一波”讨论此在的在世和共在之后,海德格尔开始对人的实质的存活状况进行一个展开的剖析。从刚开始,海德格尔就把此在的存活的独特质概念为他只不过为着我们的存活而存活,并且他多少地领悟着我们的存活。人对他的平时生活世界的领悟就是“烦”:活着不只要操劳于各种东西,还要操心于其他的人。这种“烦”其实就是人的存活的平时状况和平均状况。当然,这种“烦”并不操心自己的存活。人就注定要处身在这个平时世界之中,人具备一个肉身的存在,因此,这种“烦”就是存活的基本的情绪。它并非心理学的或灵魂状况的,毋宁说是肉身性的和处境性的。平时的基本情绪就是厌倦、枯燥与无聊,在这种情绪中,存在或者活着就象是一种负担。但,沉沦于世间生活的平时状况也提供了安全感,人处于说、看和领悟的平均状况,也就是谈话闲聊、好奇和模棱两可。
平时的情绪性的存活表明人对我们的存活的某种领悟,但却是从熟知、安全、稳定和习惯的方面关注我们的存活。海德格尔在各种存活性的情绪中拿出了一种独特的情绪性存活领悟,那就是“畏”。在《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中,海德格尔将“畏”视为对平时世界的虚无化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思想与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思想的某些差异。萨特很熟知让·瓦尔已经用一本书《克尔凯郭尔研究: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论述了克尔凯郭尔对海德格尔的影响。萨特将克尔凯郭尔的“畏”定义视为一种时间性的“虚无”,视为从存活中涌出来的自为的自由。但,对于海德格尔来讲,“畏”这种基本情绪在日常是很罕见的,由于它来自非同一般的意志和决断。为何单单“畏”被海德格尔拿出来作为最基本的情绪呢?是否只有在那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西方文化环境中,这种情绪才会对人产生这样强烈的震惊?舍勒和其他的哲学人类学家不是也把其他的非认识性的范畴(譬如爱、怨恨、同情、羞愧、焦虑等)作为存活剖析和伦理建构的核心吗?海德格尔之所以单单挑出“畏”,恰恰是由于只有它才能从存在论上显示出虚无的力量,显示出对平时存活的整个世界的超越和一跃。看着,海德格尔的“畏”的情绪更多地显示出意志的力量,而萨特径直将它等同于人的存在论的自由。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方法展示了此在展开状况的统一性,打破了传统的知、情、意的三分法的等级。看着他以对世界的操劳、实践和对存活的领悟、讲解来批判认知,立足于此在在世的平时情绪和特殊性的情绪,而高扬对向死而存活的可能性进行谋划的意志。而“畏”正是通向面对可能性和意志决断的基本情绪。这是《存在与时间》的“第二波”的内容。
“畏”使存活的平时状况失去了安全的确定的基础和依据。此在早已完全习惯的那个世界,那个与世界亲密无间的平时生活在“畏”的基本情绪中陷落了,周围世界和常人与非本己的存活都掉落了。世界失去了它的有意义的整体关联,反而,用萨特的话来讲,在虚无中显露其赤裸裸的甚至是荒谬的自在。“畏”显示了平时生活的安全感只不过对生活的实情毫无领悟和极力回避。“畏”将生活的偶在性在瞬间之中明确地呈现出来,不止是无缘无故被抛到这个世界之中,而且面对的也是动荡不安极不确定的可能性。“畏”因此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时刻”或“瞬间”。摧毁了平时的亲密熟知的世界和平时安全的生活,本真和本己的存在展示出来的瞬间,那就是“畏”的瞬间,那就是“顿悟”存活的实质处境的时刻。海德格尔将“畏”视为一种摆脱了平时的世界和别人,也摆脱了平时的非本己的领悟,进入了极端的个别化的极限情境的自由的激情,冷静的激情。海德格尔甚至说只有当大家自己在存活中历程到“畏”的时刻,只有当大家在我们的存在中与虚无相遇的瞬间,哲学才大概。
“畏”的虚无的力量并非来自外在的世界,来自外在的世界的东西会使人感到可怕,但只有来自存活本身的虚无才会使人感到“畏”。由于这个“畏”就是从死亡而来。假如仅就死亡论死亡,死亡就意味着终结和存活的不再可能。但假如从存活论来论死亡,这种不可能性是一种可能性,是尚未终结的可能性,是一直悬搁在存活前面的可能性。因此,海德格尔从存活论论述死亡的意图在于显示存活本身的纯粹的形式上的可能性。事先对死亡的清醒的领悟是回到本己的本真性的道路。也正是通过死亡,现象学所描述的此在的整体性才在一个人的彻底的个体性中完全显示出来。因此,死亡对于海德格尔来讲并非沉思的对象,更不是所谓的“悲观主义”的流露,而是现象学地甚至是先验地描述存活状况和存活结构的核心环节。
对于海德格尔来讲,清醒地面对由死亡而来的“畏”并无畏地面对死亡所打开的不确定的可能性(而不是死亡本身),这就是对存活的意义的领悟,海德格尔将这种领悟称之为良知。这个良知不是社会和公共的良知,或神学的良知,或善的缺失,或内在的道德律令的审判,而是来自“畏”的沉默的无声的呼唤,呼唤大家到本己的本真性之前,去直面存活无法避免,不可推脱的可能性。当然,良心并没告诉大家需要如何做才是本真的。这是在具体的存活处境中的决断。海德格尔毫不在乎其他人批评他是形式主义,也毫不在乎其他人批评他是伦理虚无主义。事实上恰恰相反,《存在与时间》所说的本真性具备深藏不露的伦理学动机,大家甚至可以称之为本真性的伦理学。本真的伦理学动机不只贯彻在对常人的严厉的批判之中,而且,也体目前海德格尔独特的良知定义之中。对于海德格尔来讲,只有从对本己的本真性的存活的良知出发,才能有所谓的公众的良知或社会的良知,才有所谓的伦理责任的可能性。只有从个体的本真的存活出发,才有让别人存活和让别人面对自己存活的可能性的自由。只有从个体的不可予夺的死亡出发,才有对人的存活的尊重。至于海德格尔的本真性为何是形式主义的,没提供给大家任何具体的内容,这是由于本真性的存活恰恰是纯粹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存活的可能性高于任何现实性。“第二波”从“畏”的情绪性出发,以本真的存活达到高潮。
[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