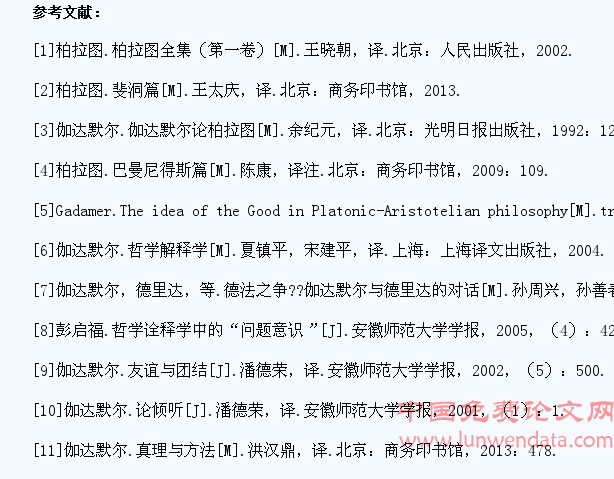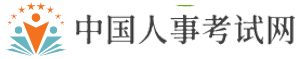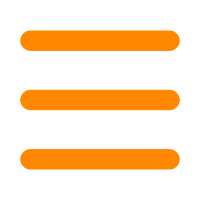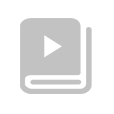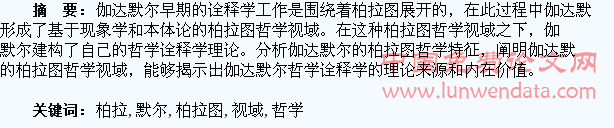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B089.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4003804
伽达默尔早期一直致力于柏拉图哲学研究,其哲学解释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伽达默尔回到柏拉图哲学,是在新的年代背景之下重新发现柏拉图哲学的积极意义,同时在柏拉图的影响下不断建构起我们的哲学解释学理论。伽达默尔追溯古希腊哲学的起点便是苏格拉底的“善”的问题,其问题的展开方法便是对话,而对话达成的条件便是语言,围绕柏拉图对话展开的是善、对话、逻各斯等一系列问题。
1、“善”的混合
伽达默尔在剖析柏拉图哲学时,就已经意识到“善”的问题是柏拉图哲学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思想体系的线索。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在为我们的辩护中提出了“善”的问题,他第一指出人的“无知”。他说:“这种无知,亦即不了解而以为自己了解,一定是最应遭到惩罚的无知。”[1]17进而通过对控告人的指责引出“善”的问题:“假如你们中间有人被觉得拥有杰出的智慧、勇敢,或其他美德,但他们却用如此的办法,那样这是一种耻辱。”[1]24可见,“善”的常识对于苏格拉底来讲,是通过“认识你一个人”而获得的,“自知者”才会获得“善”的常识。诚然,伽达默尔已经看到,与神话年代不一样的是,对于苏格拉底来讲,“认识你一个人”是认识人类自己的存在,这种人类的“善”自刚开始就不是仅仅从理论上的考虑而提出的,这里已经有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萌芽。柏拉图在后期著作的论述中进一步将理念与现实离别,由此揭示了理念在现实事物中分有些困难。分有问题是作为理念的常见性与个别事物的特殊性的内在矛盾而提出的,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具体说明了这种矛盾。伽达默尔觉得,《巴曼尼得斯篇》只是柏拉图对内在矛盾的澄明,而非对理念论的批判,柏拉图由具体事物对单一理念的分有转向了理念之间的分有,伽达默尔从这一转向中发现了柏拉图哲学中的解释学价值。在《斐洞篇》中,苏格拉底说:“我并不沉迷使自己所说的话在听众心目中看上去真实,以为那是次要的事,主要的是使我一个人相信它。”[2]49在这里,苏格拉底就已经提出澄明自己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后来表现为柏拉图在《斐莱布篇》中对混合中的“善”的探讨。
伽达默尔在此看到了一种以混合形式呈现的逻各斯的内在需要、一种“倾听”的哲学的内在本质,他说道:“大家所关注的唯一对象就是‘事情本身’,即‘真的善的东西’。”[3]柏拉图在吸收借鉴了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观”和巴曼尼得斯的“一与多”的矛盾,提出理念数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阿那克萨戈拉的“混合”与“离别”思想。对柏拉图来讲,“善”存在于混合之中,“善”的混合作为一种真的的混合包括尺度与秩序,同时,这种混合作为事物是什么原因而被柏拉图提出,这与伽达默尔理解的前见是相对应的。在《斐莱布篇》中,苏格拉底就真的的推理和正确的建议、快乐相比何者更为出色的问题展开了对话。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觉得快乐同常识一样,“它们永远是一又是相同,既不会产生也不会消灭,它一经开始就永远存在,它是最确定的单一,然而它后来可以存在于有产生的无限多的事物中――它是一种可以同时在一与多中发现的相同的一。”[1]182
柏拉图提出通过数目和尺度来确定这个一“是什么”,而作为混合中的尺度和秩序可以是不同比率的,这恰恰展示了一与多的矛盾,柏拉图意在通过数来确定居间的东西,这就构成了柏拉图哲学系统的整体视域,而这也是柏拉图寻求灵魂和谐、宣传哲学教育的宗旨所在。“善”的问题在伽达默尔看来,既能反映出柏拉图哲学的一体性,又能作为构建哲学解释学的范型,由于伽达默尔在“混合”之中看到了某种特殊的解释学经验,而这种“混合”在理解的过程中表现为视域之间的融合。另外,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巴曼尼得斯对少年苏格拉底的理念“分有”说的诘难促进柏拉图转向了理念之间的分有,从而转向了逻各斯的问题。巴曼尼得斯指出了理念“分有”的困难,却未否定理念论。他觉得:“如若由于顾到目前刚讲的所有困难,与其它类似的困难,否定有事物的相,如若他关于每一类事物不分别相,他将不可以将他的思想向着任什么地方所转移,由于他不承认每一类事物的相是恒久同一的,并且如此他完全毁灭了研究哲学的能力。”[4]同样地,伽达默尔觉得“分有”说的困难仅仅揭示了一种数的结构,而这种数的结构“一直指向与某物的同存”[5] 。这种存在着“一”与“多”的矛盾逻各斯问题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同基础,亚里士多德正是由此出发区别了两个本体,并提出了实践的智慧。由此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理解的实践智慧虽然直接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但从“善”的问题的始源性层面来看,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柏拉图哲学有更深的渊源。
可见,“善”的问题构成了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视域的线索,而柏拉图所提出的混合问题,经过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改造后,成为其视域融合理论的要点。柏拉图对混合问题的揭示,或者说,对“善”的问题的探讨是通过对话的方法完成的,因此,柏拉图的对话也是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的一个要紧方面。
2、对话的开放性和问题意识
柏拉图是通过对话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因而对话在柏拉图哲学中占据十分要紧的地方。柏拉图的对话以“善”的混合为起点,伽达默尔从这种混合中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解释学经验:“大家被某种东西所支配,而且正是借用于它大家才会向新的、不一样的、真实的东西开放。柏拉图把这一点说得非常了解,他巧妙地把躯体的事物同精神食粮作了比较:假如大家能拒绝前者(比如,依据大夫的建议),那末大家一直早已同意了后者。”[6]9在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一直试图引导他们在对话开始之前就某一方面达成一致,且不论对话双方是现实的苏格拉底与其他人的对话,亦或是柏拉图在主观上的虚构,伽达默尔所要强调的是这种作为对话首要条件的“善良意志”,即承认对话双方的前见及地位。因此,对话一直需要“两者都具备相互理解的好愿望”[7]20。在柏拉图的文本中,苏格拉底通过对话的方法,使得他们承认我们的“无知”,同时认识到“X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柏拉图的对话一直维持一种开放性,真理在这种开放的对话中发生。 在柏拉图对话中,作为引导者的苏格拉底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对话理论中成为一种“问题意识”,伽达默尔特别强调问题在对话中的优先性,正确问题的提出规定着理解的方向。他说:“作为柏拉图的学生,我特别喜欢有关苏格拉底同智者们争论、用他的问题使他们陷于绝望的描写。”[6]12柏拉图对话是作为文本形式而展示的,与现实的对话不同,文本对话是在读者主观内重构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读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时间距离。因为时间距离所导致的疏异化妨碍了读者的理解,因而读者的问题意识就看上去非常重要,这不只可以限制对话展开的范围,更可以引导对话展开的方向。正如苏格拉底在《斐洞篇》中强调的,“假如问题提得正确,人家是能完全正确地回答的。”[3]23问题意识在对话中作为引导者可以将对话结果引向海量可能性,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对话正是一种以适当的问题提出为起点,基于一与多的关系的辩证过程,“是一种伙伴之间平等地展开的商讨式的对话”[8]。无论是柏拉图的对话还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话,都是参与“善是什么”的问题。虽然有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并未有直接的结果,却展示了这种活生生的文学形式的特点。对话双方就某一个问题达成协议,即获得双方的一致建议,这是对话发生的功用所在,这种一致建议介于对话双方之间,是一种无限可能性的存在。
诚然,伽达默尔在其早期对柏拉图对话的探讨中既揭示了柏拉图对话的伦理维度,同时也展示了对话在日常的应用性。伽达默尔晚期论述“友谊”和“团结”等问题的文章正体现了这一方面。伽达默尔觉得“友谊”具备三个特点:第一,朋友之间存在着互相被信赖的真实关系;第二,朋友之间一直存在着差异;第三,朋友之间的一方一直能在他们找到自己的存在,或者说赋予他们以存在,即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自我的认知。当然“友谊第一就是大家与我们的一致。大家需要如此的首要条件,才能与别人联系在一块”[9]。在这里,“与我们的一致”正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一个人”的解释学内涵,即对前见的承认,或者说,对柏拉图提出的“善”的混合的承认。伽达默尔从柏拉图的对话中认识到,对话的真的价值并不是在于发现双方的一体性,而是承认双方之间的差异,并达成不同视域之间的融合。这种一体两性生活特点的三要点正是柏拉图理念论的三要点:存在、相同、相异,伽达默尔在柏拉图那里认识到对话正是“一体性”日常的存活方法,对话不是为了找到双方的类似之处,而是为了交流双方的差异,并以辩证法的方法获得自我存在与自我认知。因此,对于伽达默尔来讲,即便在不同性格和不同政治观的人之间,对话也是可能的。这就表明了对话一直开放的,即问题一直维持打开与对话的结果存在着无限可能性。
在柏拉图对话中,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其他对话者,在对话的过程中都有将我们的思想完整表达出来,因而这也显现出了使得对话达成其意义的另外一个要紧的条件,即“倾听”。“倾听”不止是“听”自己的前见,与自己维持一致,同样是“听”他们的诉说。伽达默尔觉得“听”与“观”不同,“倾听”的对象是在隐藏于文本背后不可见的东西,“假如倾听涵盖了大家可以想象的整个宇宙,它便意指语言。”[10]伽达默尔指明了被倾听的话语具备肯定的意义,文本不可以像话语那样,其意义在平时交往过程中可以配合语音语调、肢体动作完全表达出来,“他们缺少对活生生的会话的明显校正”[7]21。在理解的过程中,向文本原意的追溯被伽达默尔视作极端状况看待的,根据伽达默尔的说法,大家所理解并不是文本的语文学含义,而是寄于文本中的意义,这种意义正是语言所具备的特质。在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中,逻各斯问题正是在话语的意义上而提出的,是柏拉图通过对话来说明的。
3、指向现实的逻各斯
柏拉图对话涉及的是语言的问题,具体来讲,便是逻各斯的问题。同样,伽达默尔的语言解释学也是以此为主线,伽达默尔觉得“可以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11]。在伽达默尔看来:“可以理解的东西,就是达乎语言的东西。”[7] 9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通过分有构成逻各斯,而逻各斯作为讲出的话语具备一种可以被“倾听”的特点,逻各斯是对事物的本质陈述。逻各斯作为话语,其意义是开放性的,同时,它一直指向个别的特殊的现实事物。显然,受柏拉图语言观的影响,伽达默尔充分意识到逻各斯与现实事物的离别。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分有”的困难正揭示了这一点,对于柏拉图来讲,逻各斯是理念之间通过分有而构成的,因此,逻各斯一直指向具体的事物,而不是空的形式。因为理念的常见性需要单一理念一直指向某一类事物,这就必然导致了个体事物对单一理念分有些困难,从而促进柏拉图转向了理念之间的相互分有。理念通过分有所构成的逻各斯则是作为一种总和数而存在,它具备单一理念所没的意义,正是因为逻各斯,语言才可以显示出其整体的意义。
对于伽达默尔来讲,理解在于把握整体意义,文本意义是一体的和连贯的,整体意义构成文本的视域和背景,唯有借用于此,文本中部分不容易理解的内容才可以获得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精心构筑的理想城邦正是其理念结构的一种假设。无论柏拉图的理念与个别事物以何种方法发生关联,都反映了柏拉图所觉得的理念一直同感性世界存在着某种联系,理念之间的和谐使得逻各斯可以作为多中之一而存在,这依靠于灵魂的统治。柏拉图在《斐洞篇》中提出,话语作为一种表达方法一直在先地通过“说”而呈现出来。而主体倾听的过程同时就是理解的过程,主体通过理解自己而深思他者,又通过理解他者而深思自己。逻各斯内在地表现为“善”的,一直不断地处于趋近真实事物的过程中。伽达默尔注意到由逻各斯所构成的问题本身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允许不一样的个体有不一样的理解。正是因为这种语言的特质,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讨论因不断地否定、修正而趋向适当的辩证过程而成为真的的讨论。伽达默尔通过对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很多不合逻辑之处进行现象学办法的讲解,展示了真实的对话结构:真前见和假前见的交织就好似《斐莱布篇》中苏格拉底所言的常识考察之前状况是全部的快乐与理智的混合,而区别是在理解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伽达默尔所重视的不是逻辑上的一致性,而是意义上的一致性。理解一直需要依据前见而进行,对前见的承认也为对话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在生活世界中,语言是作为个体的人进行交流的媒介,通过将蕴含于人类一同语言中的一体性澄明出来,不止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纽带,而且是个体的人进行自我深思的必要条件。 依靠实践理性通过对话方法确定适当的一致建议,由此,伽达默尔在对话过程中融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虽然柏拉图在逻各斯问题上并没深入到实践的范围,却触及了语言所具备的这种功用,亚里士多德随后深入其中,提出了实践哲学。可见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在逻各斯问题上,指出了语言与现实的关联,同时表明了逻各斯的开放性,这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铺平了道路。这种指向现实的逻各斯内在地表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内在关联,无论伽达默尔是由亚里士多德哲学追根溯源而回归柏拉图哲学,或是由柏拉图哲学按部就班而到达亚里士多德哲学,都表明了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是其整个古希腊哲学视域的初步构造。
4、结语
在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中,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无知”出发,以对话的方法,在混合之中探寻“善”的住处,而在对话的过程中,说明了逻各斯的问题。柏拉图“分有”难点所揭示的“一何以是多”、“多何以是一”的问题,也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重点。而这一逻各斯问题是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视域在其哲学解释学中发生融合的媒介。柏拉图通过对这种理念数结构(和谐、比率和开放性)的揭示,探讨了“善是什么”的问题,同时揭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诚然,柏拉图通过“一与不定之二”的矛盾揭示了逻各斯的问题,逻各斯作为意义规定性的集合,其意义是独立于构成逻各斯的单个语词的意义。柏拉图通过对概念的划分揭示了逻各斯意义的开放性,而非旨在构建一套完整的逻辑演绎系统,这是柏拉图对话所要揭示的真理,而这也正是逻各斯本身的缺点所在。伽达默尔在如此一种柏拉图哲学视域之中,将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与解释学融合,并提出了“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伽达默尔同样不是在用一套完备的范畴体系来规定“理解是什么”,而是旨在解决“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反映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所受柏拉图的深刻影响。